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中几则基本材料的疏证
- 文化传承
- 2024-11-23 17:08:10
- 116

前言近年来,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领域一改往常的沉寂局面,新资料不断涌现,旧资料不断被重新识读,研究课题也日渐多样化,从而形成了渐趋热络的局面。在对中国低温古代铅釉陶器资料爬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相关......
前言
近年来,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领域一改往常的沉寂局面,新资料不断涌现,旧资料不断被重新识读,研究课题也日渐多样化,从而形成了渐趋热络的局面。
在对中国低温古代铅釉陶器资料爬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相关讨论时,一些基础资料的引用还存在不少偏差,有的甚至是被误读和曲解。尤其是几则关乎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起始年代和烧造地点等关键问题的核心资料,被辗转征引而不辩究里,以至于以讹传讹而影响深远。论据的讹误直接导致论点的不严谨甚至不可信,不仅使前人的研究成果被忽视,也使得本可避免的错讹长期地反复出现。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几则典型的误读和曲解加以梳理,并对几则基础资料的准确性加以厘定,以期正本清源,俾使有关论者在新的讨论中对基础资料和核心论据的使用更加精准,结论更加可靠。若有唐突,尚祈指教。
一、战国起源说所依据的洛阳金村大墓的墓主问题
在临淄战国陶罍出土并获确认之前,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起源诸说中,战国说者均以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铅釉陶罍作为最重要的证据之一。而国内外相关论者在涉及该陶罍出处时,均言出自洛阳金村韩君墓。此种现象甚为普遍,兹举有代表性的三例:
1、日本学者:“(纳尔逊美术馆)绿釉蟠螭纹壶,传河南洛阳金村韩君墓出士,战国时代”。
2、台湾学者:“传洛阳金村韩君墓出土的绿褐釉螭纹盖壶亦属战国时期铅釉陶的珍贵实例”。
3、中国大陆学者:“传世文物中,笔者仅搜集到一件与本文所论釉陶罍(笔者按:指临淄战国墓所出者)近似者,现存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rt),相传出士手洛阳金村•韩君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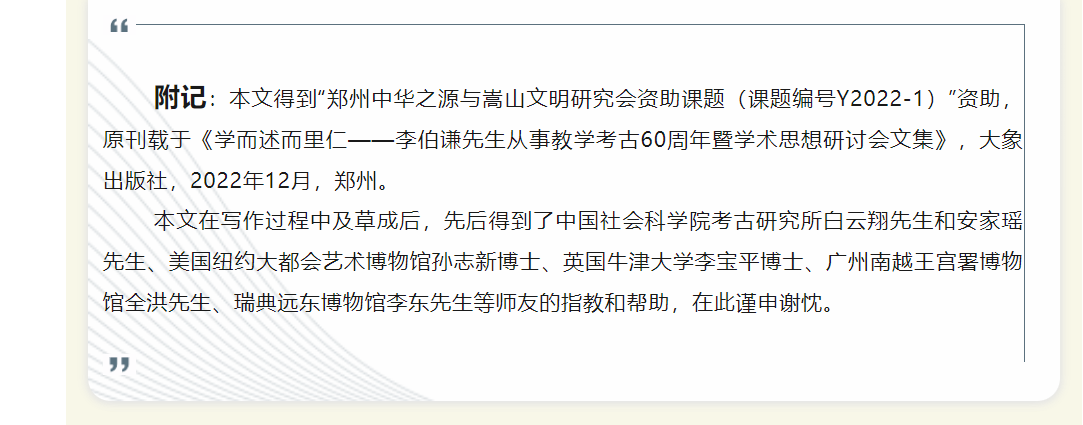
金村古墓最基础最经曲的西本著述,分别出自有着加拿大传教士身份的怀履光(williamCharesWhite)和日本学者梅原未治,这两部著作可谓亡羊补牢,差堪补憾。除了记述墓葬形制、著录出土文物之外,两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墓主人认定为战国时期的国君,梅原未治认为是秦君,怀履光则力主韩君。前者是因为银器的针刻铭文中有“三十七年”字样,被梅原未治错误地释读为秦始皇三十七年,继而认为是秦君墓葬。后者主要是根据金村大墓流出的翕氏编钟铭文中出现了“韩宗”一词,被硏究者认为属于韩国。接替安特生出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则通过对弱氏编钟等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对梅原未治秦墓说进行驳议之后,论证了金村古墓是韩国贵族(他认为有可能是王子)墓葬的可能性,从而使金村古墓韩君说在欧美学术界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最早提出韩君墓之说的是马衡等中国学吉。此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和日本学术界风行一时,但很快有学者对此提出驳议,认为金村大墓乃战国时期东周墓,唐兰先生、陈梦家先生是其中的代表。此后,又有中国学者指出,战国时期的洛阳是周王所居的成周,是名义上的周王朝中央政府所在地,无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还是从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考量,地处东周王城的金村大墓,是不可能属于秦晋韩等诸候国君的。换言之,所谓的秦君墓、韩君墓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最大的可能,乃是属于东周君或者周王室。俟后,李学勤先生通过对金村大墓出士铜器铭文的考释,尤其是被持韩君说、秦君说者认为涉及韩国与秦国历史的铭文的辨析,认为金村草萃联既不是秦墓也不是韩墓,也不是东周君墓,而是东周王室的墓葬,可能包括周王及附葬臣属。被盗掘的八座大墓,其时代均为战国时期,下限迟至战国晚期。此说提出之后,学术界基本再无异议。洛阳市文物考古部门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综合国内外学术成果,已经把金村古墓群确定为东周王城的王陵区之一,并据此制定整体的保护研究规划且获国家主管部门认可。
因此,金村大墓应该是战国中晚期东周王室墓葬。此种认知至迟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提出,到八十年代时已基本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秦君墓说早已销声匿迹,东周君墓说也已经式微,惟韩君墓说则因辗转征引以致以讹传讹,在日本和台湾尚有一定余响。中国大陆学者当中所持或者引述韩君墓说者,大多源自对日本学者和台湾学者著述的辗转征引。在此问题已经被破解半个世纪左右之后,此种以讹传讹的现象当应避免发生。
二、西汉中期起源说所依据关中汉墓的资料出处问题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不可胜计的低温铅釉陶器的出土,使得中小型汉墓的发掘者和报告的编写者不得不对其进行考古学的分类与排序。这项田野考古研究最基本的工作,导致考古学界通过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研究,推定出了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年代最早的低温铅釉陶器,出自关中地区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中。此为西汉中期起源说的最初来历。
“西汉中期起源说”的形成立足于当时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立论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力图以科学的资料为基础,提出基础坚实的学术认知。这一在当时并无争议的学术观点,被俞伟超先生写入北大考古专业的讲义中之后,得以在全国考古界风行,并被古陶瓷界和科技界所认可,然后为诸家征引,几为不易之论,从而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陶瓷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三部权威著作,成为在学术界影响最为广泛且最为持久的观点。
人们对这一观点长期深信不疑,一方面源于大规模田野考古中的发现与之基本吻合,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北大考古专业以及俞伟超先生本人学术素养的信服。这一观点唯一的、也是严重的缺憾,在于其基本资料至今尚未刊布,所出究竟何物,具有何种特征以及出土环境如何,俞先生并未明示,征引者也无人探究,这批资料迄今仍付阙如,发掘者、整理者均已难述其详,甚至于资料的归属存放也不了了之。因此,该批资料中诸如器物形态及其组合关系、外观特征、烧制工艺等等关乎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最基本信息,我们均已无从得知了。如此一来,西汉中期起源说的论证过程就成为无本之木了——尽管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学者对这一学术观点进行过论证,而且在新的田野发掘资料的出土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尤其是具有可靠并且完备的考古信息的战国低温铅釉陶器已然出土刊布并加以论证的情况下,西汉中期起源说的论证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必需了,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这一学术观点的内涵至少是不完备的。
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起,陕西省文物局组织专门机构,抢救整理1950年代的考古发掘资料。笔者经仔细核校,发现书中收录的汉代墓葬(含新莽时期)中,包括了西安近郊及关中地区发掘的汉墓68座,其中共有16座出土有施釉陶器。这16座墓葬中,大体可以判断属于西汉时期的约有8座。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该批资料详略不一,准确度互有参差,因此尚不足以对其年代和随葬品组合关系等基本考古信息做出准确判断和归纳,遑论其所出低温铅釉陶器的器物形态、工艺特征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尽管无法确认该批墓葬是否属于俞伟超先生所说的那一批关中西汉武帝时期墓葬,且资料尚有不少缺项,但差堪补此缺憾。同时,我们也殷切期待,当年俞伟超先生作为立论根据的那批西汉中期墓葬资料,能够从故纸堆中被辨识并刊布。
我们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苛求前辈学人而是恰恰相反,是在向先贤致敬的同时,力图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得失,以使前人探索的意义得到彰显。
三、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的带釉砖瓦的属性与年代问题
至于所谓的低温铅釉陶瓦,器型包括绿釉莲花纹瓦当(97T13GC①:21)、绿釉板瓦(97T13GC①:29)和绿釉砖(97T1GC①:3),有的化学成分和理化性能的确属于低温铅釉系统,也的确出自该遗址,但却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王朝的层位,属于南汉皇宫的建筑构件,其时代为公元917—971,与西汉中期相差千年有余。彼时,低温铅釉用于建筑材料已蔚然成风,故建筑基址中出土此类器物已不鲜见,比如同样位于广州地区的同为南汉皇室建筑的康陵陵园建筑遗址内,就出土了低温铅釉筒瓦和瓦当。而南汉前后遍布全国其他建筑遗址诸如唐大明宫遗址及渤海国遗址,南汉之后的巩义北宋皇陵遗址及宁夏西夏王陵遗址等,均有低温铅釉的建筑构件出土。但有汉一代,尚无此例。
故此,关于南越王宫遗址出土低温铅釉建筑材料的问题,可以廓清为两点:
一是汉代地层出的带釉筒瓦是钠钾碱釉而不是低温铅釉;
二是低温铅釉瓦和瓦当均出自该遗址的南汉地层而不是西汉。
以往的误解,源自对釉的属性和建筑构件的时代产生了严重误判。
四、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铅釉陶罍的可信度问题
前文已述,战国起源说者把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绿釉陶罍作为重要证据。较早把该陶罍作为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来论述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先是长谷部乐尔在其编著的《中国美术》系列之《陶瓷卷》中,收录该器并注明传出自洛阳韩君墓。俟后,弓场纪知在其所著《汉代铅釉陶器的起源》一文中,把这件被认为属于战国晚期的文物,作为他中国铅釉陶器战国起源说的重要证据。台湾学者谢明良在其相关论著中,引入了日本学者征引的资料和观点。而此后中国大陆涉足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学者,则对该陶罍的可信度表示存疑。所以在相关的讨论中,大陆学者甚少涉及到该件陶罍。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大陆学人的视野所限,但我更愿意相信是源自田野考古学家对文物资料出土背景的谨慎。由于该绿釉陶罍不是正式发掘出土品,其出土地有待科学辨析,出土单位无法确认。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对象的真伪、时代以及出土地都存在不确定性,故中国考古界对其辨伪、断代问题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尤其是洛阳金村文物的流失背景十分复杂,被冠以金村出土文物的甄别和辨伪一直是中国考古界议论的话题。因此之故,在无法亲临观看甚至无法获取更详尽资料的情况下,更不愿遽断。
台湾学者曾确表示,“(弓场纪知)宣称纳尔逊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藏品传出土于洛阳金村、东京博物馆藏品传出土于安徽寿县,对此本文不予采信”,率先对其出土地表示质疑。俟后,临淄齐故城战国铅釉陶罍的确认者立足于有准确出土地点和确切的考古层位关系的发掘资料,也基本否定了纳尔逊藏品出土地的可信性。作者指出:“现存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rt),相传出土于洛阳金村‘韩君墓’。该器的形制、装饰、釉色等均与临淄出土釉陶罍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当为同类器物。惟该器为双耳,临淄所出为四耳,耳的形制亦略有区别。洛阳是我国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考古工作众多,在发表的考古资料中迄今未见同类器物出土。因此,传该器出自洛阳的说法只能存疑”。
有鉴于战国晚期与西汉早期文化的延续性,尤其是在作为当时文化中心的河洛地区,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陶器形态演变比较缓慢,在缺乏明确的出土背景下,试图准确进行年代定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一度对以纳尔逊陶罍来论定战国起源说比较谨慎,而倾向于用有明确出土单位的文物来做立论支撑。因此在文章中,我同样表达了这种谨慎态度:“(战国)说的根据,是目前已流传至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据传是出自洛阳金村和安徽寿县的战国墓葬的几件铅釉陶器。另外,韩国某收藏家的藏品中,也有一件铅釉陶单耳杯,造型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原始瓷器被极为相似。但这几个案例均缺乏可靠的出土背景,其年代问题似不宜遽断。何况,战国晚期与西汉早中期的某些器形在无可靠出土资料的情况下是较难以区分的。故铅釉陶器起源于战国之说,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但很显然,与前述几位存疑的侧重点不同的是,我强调的是该陶罍的时代,而不是其出土地。
如果说,此前我对纳尔逊收藏的据传出土洛阳金村大墓的战国绿釉陶罍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临淄齐墓出土的绿釉陶罍,则把我的疑虑基本冰释了。临淄齐国墓葬战国陶罍甫一出土,我即寻求相关资料,将两者加以比对。比对的结果是:
1、器物形态的一致性:两者均为广肩、鼓腹、圈足并带盖的球状轮廓,盖顶上均带有四个钮状捉手,明显是模仿青铜礼器的造型;
2、釉面的一致性:两者外表均施釉,釉色青中泛黄,有细碎开片,光照处有银釉闪烁。釉面不匀,局部有斑驳;胎釉结合不牢,局部有脱釉;
3、胎体的一致性:两者露胎处,均显现出灰色胎体。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灰胎低温铅釉陶器,与两汉时期绝大部分呈现红色的胎体极为不同;
4、烧成技法的一致性:从灰色胎体可以推测出两者均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应该是和普通灰陶器甚至原始瓷器同窑,在同样烧成气氛中烧成的;
5、装饰的一致性:两者均是在肩部和上腹部各规划一条装饰纹带,装饰母题是战国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蟠螭纹和云雷纹;
6、出土环境的一致性:金村古墓均为甲字形大墓,有些还有殉马坑,属于高等级贵族甚至王室墓葬。临淄安乐店战国齐墓也是甲字形,全长超过20米,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主人应是齐国的贵族。
另外,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产地一致的可能性。从前述诸方面判断,很有可能是同一个窑场烧造的。
据此
我对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陶罍的基本判断是
年代
战国晚期
釉的属性
低温铅釉
归属与性质
上层贵族随葬品
出土地
可能来自洛阳东周王室墓葬
基于此判断,我认为,对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陶罍的所有疑虑可以基本打消。临淄战国齐墓低温铅釉陶罍的出土,不是否定了或者取代了前者,而是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证实了此前对于其年代和性质的判断,两者之间是互证关系而不是否定关系。由此,也显示出了以此立论的战国说的学术预见性。
五、大英博物馆典藏战国陶罐的出土地问题
大英博物馆典藏战国陶罐也是被国内外研究者广泛举证的一件著名文物。因其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典藏的同类器物在外观上具有品著的一致性,日本学者也最早把该类文物进行汇集和比对研究。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大英博物馆的该件陶罐被认为是据传出自洛阳金村,此说被众多中国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辗转引用,是以在目前的汉语系著作中,相关论述均沿袭此说。
在进行中国吉代低温铅釉陶器的分类和溯源的工作中,出于谨慎,我对该件陶罐原始著录和出处进行了检索,惊讶地发现,在欧美学者的著作中,此器被认为出自河南浚县,而不是亚洲学者所说的洛阳。尤其是大英博物馆官方主持编纂的藏品图录,其藏品的年代、出处、来历等信息应该是最接近档案的第一手的材料,应该比一般的著作或论文可信度更高一些。
事实上,即使是在盗掘事件发生的当时,怀履光就已经意识到了他所收购的所谓的金村大墓出士文物当中有很多是不可靠的,以至于他自己就列出了一份存疑的清单,瑞典学者高本汉也指出怀履光著录中的可疑之处。既往的金村文物群概念,大多是通过这种推测、附会的“加法”的途径所形成的,以至于越来越庞大杂芜。近年来,有中国学者提出,在“加法”已不可为的情况下,善用“滅法”是接近真实金村器物群的必要途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让这件陶罐,也许就为“减法”的应用提供了极好的案例。
循着这条线索和思路,再来观照被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同类藏品,我们会发现这个误会还在延续,而且如出一辙。大英博物馆藏品之所以被有些学者被误会成洛阳金村古墓出士,显然是受到了纳尔逊美术馆这一做法的影响。但大英博物馆本身却出言递慎。因此在介绍该件陶罐的同时,该馆也把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同类臧品并列,明确指出是“另一个例证”,其中暗含的信息,恐怕不仅仅把两者归为同类同时代的器物,应该是包括了出土地,也就是说英国藏家在暗示与美国的藏品属于同一个出土地。
事实上,大英博物馆的图录介绍中,把美国的藏品标注为Sedgsick的收藏,而大英博物馆自己的藏品,在相关的著录中也被注明是SedgsickCollection。两相对照,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两者属于同一个收藏者,而且是同样的形制、用同样的品格,缘何分属英美两家博物馆后出土地却分厲浚县辛村与洛阳金村?很显然,误听、误译以及附会都可能是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件来自中国中原地区分藏大西洋两岸的绘彩铅釉陶罐,极有可能出自辛村而被加入金村器物群的。明确了这一点,就应该采用减法,将其从金村器物群中剔除。
这件陶罐不是出自洛阳金村大墓的另一个旁证是,瑞典学者在进行远东古代玻璃器专题研究时也把该件陶罐列为讨论对象。在涉及到该件陶罐时,作者仅仅很明确地注明是Sedgwick的收藏,而没有任何涉及金村大墓的信息。相反地,其他所有出自金村的资料,都有明确标识。设若该件陶罐属于金村大墓,作者不可能毫无提示甚至暗示。
因此可以判断,大英博物馆典藏的这件战国绘彩类低温铅釉陶罐,经检索其藏品档案并结合考古学史资料,应该是出自河南浚县辛村,而不是洛阳金村。日本学者的误听或误译被中国学者误引,影响持续至今。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1930年代前后四次发掘的浚县辛村,文化内涵包括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和西周时期的卫国贵族墓葬,已经刊布的考古资料中并无东周时期的遗存,学术界对辛村的认识也仅限于西周时期的卫国。因此,大英博物馆入藏的这件被认为属于战国时期的绘彩陶罐,似乎应该与1930年代原中研院史语所在没县辛村的考古发掘主体内容无关。但实际上,据发掘者石璋如先生回忆,当年曾经发掘清理出随葬品丰富的汉代墓葬。近年来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在辛村遗址新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时期遗存,说明辛村一带出上战回两汉时期的文物是很正常的。
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浚县辛村的古墓葬盜掘异常猖獗,当地已经形成了官匪勾结的盗掘体系。连李济都感慨总部设在巴黎的古董商在中国北方各省都设立了分机关。史语所之所以在辛村进行连续多年考古发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阻止当地的疯狂盗掘。这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国两汉陶器在三十年代从辛村盜掘并辗转流传到欧美,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北朝铅釉陶器燒造窑址的资料问题
近年来,河北临漳发现了一处名为曹村窑的古代窑址,调查者和试掘者均认为该窑址的烧造年代为北朝时期,并进一步断言,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士陶瓷器应该是这个窑口的产品。科技界也有人对样本进行了测试,确认了一批低温铅釉器四。果如是,则自应视为北朝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重要资料,自然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因为迄今为止,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烧造遗址,尚无一例明确的考古发现。曹村窑的发现一旦得到确认,必将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成果。
但通过对己刊布的相关资料和论述的梳理分析,我个人认为,虽然曹村窑的资料对寻找北朝时期低温铅釉陶器的烧造地点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线索,但相关论著在窑址的年代论定、出土文物的层位关系以及相对年代推定诸方面,曹村窑遗址的定性还有得三其础性工作有待展开,目前尚不具备认定为“经考古发掘的烧造低温铅釉陶器的北朝窑址”来看待的基本要素。更进一步地,以此来论定北朝时期低温铅釉陶器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指标,显然是缺乏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的。换言之,在目前资料的基础上,确认曹村窑是北朝时期烧造低温铅釉陶器的专业窑场,尚显言之过早。
首先,论者以曹村窑采集的酱釉碗与东魏高雅墓出士的天平四年(公元537年)酱釉碗造型一致为论据,认为“曹村窑的时代上限不会晚于东魏”,这一表述,与考古学判定年代的逻辑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器物比附成立,恰好说明曹村窑的年代上限不早子亦即相当于或者晚于天平四年而不是相反。其次,《河北省临漳曹村窑址初探与试掘简报》这个标题本身就不符合考古简报的基本要求,《简报》中没有发掘区位置图、发掘地点的平剖面图(经查,简报中的曹村窑剖面图实为文物勘探图,而非发掘简报必须的发掘探方剖面图),也确实缺少考古简报的基本要素。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所有的出士遗物均没有出土单位和器物编号,没有层位关系,其相对年代根本无法排序。尤其是具有重要年代意义的铜钱,无法从简报中得到任何出士单位的信息,因此也无法与任何遗物建立科学的关联关系。包括灰坑和窑炉在内遗迹单位,其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均无法从层位关系中得到解释。
因此,通过已经发表的资料,很难把这次活动定义成科学的考古发掘。这两篇文章所刊布的资料,只能视为采集品,其结论也无法用科学考古发掘的方法去验证。同样,对该窑址标本的各项测试中,对象是曹村窑的八件标本,但均没有出土单位和出土层位,更没有路物编号,故测试结果与窑器物年代和窑址年代的推断之间,逻辑关系是不成立的。有鉴于此,我并不认为目前已经可以从考古学和科技检测角度认定曹村窑的北朝低温铅釉窑址厲性。
考古发掘与田野采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遗物的原始层位关系,缺失了层位关系的文物,在考古资料的整理阶段一律会被归为采集品,这是田野考古的惯例和基本要求。因此,有关曹村窑的所有标本,目前看来均应被视为采集品,而不具备考古发掘出土品的基本属性。以此为论据所得出来的有关北朝时期低温铅釉陶器烧造地的观点和结论,至少是不严谨不严肃的。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相信,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一带,既是北朝肘期低温铅釉陶器集中出土的区域,也极有可能是重要的烧造区域,正如宿白先生对太原大同一代北朝墓葬出土低温铅釉陶器做出的“其产地应该在北齐北都附近”的科学预判一样。我们同样相信,墓葬出土文物与田野采集文物所提供的线索,显示出在该区域取得学术突破、填补学术空白的极大可能性,包括曹村窑属于低温铅釉陶器专业窑场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这种学术假说和学术预测进行证实的唯一途径,是科学严的考古发掘以及资料的整理和编写,在此基础上,从最基本最确凿的原始资料出发去申述学术观点,而不是舍本逐末。
本文链接:https://gwsc.zzxfkm.com.cn/328310280160.html
